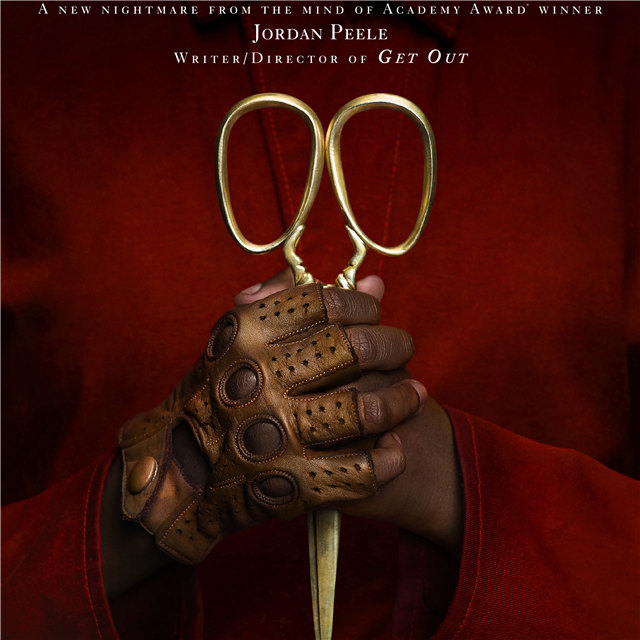我有时在想,一部好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对于文艺上的审美各有倾向,我们无法用一种既成的理论作主观判断。如果脱开美学上的讨论单就内容而论,我认为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它应该充分揭示世界的荒谬和人性的复杂,且在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具有包容的态度。世界如此荒谬,人性如此多变,面对这一切,我们选择“不选择”,这是一种观世相的态度,到头来也是一种理性且包容的方式。这正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阿尔贝·加缪所提出的。
影片《远离人迹》改编自加缪的短篇《主人》,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之于生活荒诞性的深刻表达,而其中亦不泛加缪个人的影子。我没看过小说,但就影片所传达出的思想和内容而言,它跟加谬的人生有诸多暗合之处,而影片也对加缪思想作出了充分且完美的影像化诠释。
首先,由影片我们得知,维果·莫特森扮演的男主人公达吕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且是早期法国和西班牙移民的后裔,这跟加缪的身份是一致的。影片中的达吕是个老师,而加缪在二战期间也曾到阿尔及利亚教书,在这期间他构思出了他唯一的长篇《鼠疫》;达吕二战时在意大利参与了反抗法西斯的作战,且是个少校,加缪虽没打过仗,但在战时加入了北方解放运动的抵抗组织,也主办过多份卓有成效的“反动”报刊。达吕的夫人在十年前就去世了,加缪的第一任妻子也早早离开了他。作品中人物的经历多多少少带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这并不奇怪,维果·莫特森虽然长得不像阿尔贝·加缪(加缪长得更像亨弗莱·鲍嘉)但在影片中他烟不离手的习惯和抽烟的状态像极了加缪。
是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荒谬,还是荒谬永远存在?加缪认为世间的混乱和荒缪是不可避免的,而人作为一种存在并没有确然的意义与目的。而当人面对荒谬的世界时,唯有以爱、包容和同情心面对这一切。
在影片中我们便看到了一个荒谬的世界。那个阿尔及利亚土著为了保住家中仅有的粮食而杀死了自己的堂兄,而堂兄那边的兄弟为了复仇又要杀死他,而他是家中长子,为了避免他死后自己的弟弟又为他复仇,于是决定接受法律的自裁从而脱离家族仇杀的怪圈。面对兄弟之间互相仇杀的荒谬,他选择用自首这种荒谬的行为去化解。而身处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达吕,不但存在着身份认同的困难,也存在着由此产生的政治上的迷惘。他是法国人,但又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是支持政府军呢,还是支持当地的解放阵线呢?他过去的很多战友都参加了解放阵线,为这片土地的独立而牺牲;而在政府军看来他又是个预备军官,是个地道的法国人,应该支持法国的继续殖民。但在影片中达吕和阿尔及利亚土著不但被村民追杀亦被两方势力所撕扯。现实中的加缪又何尝不是。
加缪与萨特的论争,归根结底是人性高于政治,还是政治高于人性的论争。加缪虽然隶属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但他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对于信仰与革命,他表现出了那个年代少有的清醒,他说“我们这几代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信仰,这正是悲剧所在,面为革命即使成功,也仍然向我们展现出恐怖的一面。”加缪赞赏苏联的共产主义,但听到遍布于西伯利亚的“古拉格群岛”时,他动摇了信仰,“基于政治理由的屠杀变成了一种临时的道德观,掌权的革命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以人类未来的幸福的名义作辩解。”他认为“苏联是一片奴隶的土地”。加缪在政治上跟他的左翼阵营渐行渐远,而面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时,他更是得罪了所有的人。当时的法国知识界大多反对殖民主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加缪不置可否;而对于国家主义和法国人看来,加缪又是个十足的叛徒,因为他并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不管是苏联问题,还是政治上的左右派之争亦或跟他悉悉相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加缪都处于左右不讨好且极为孤立的荒谬处境。面对世间的荒谬以及世态的正与反之间,加缪不愿选择,但加缪有态度。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人性高于革命,同情和爱心高于政治的纷争。
通过加缪的人生及他的思想,我们便可以了解影片中的达吕的所作所为。见到那个阿尔及利亚犯人,他首先为他松绑,为他倒水、做饭、喂药,甚至一路上保护他。达吕不愿意送这个犯人去坦吉特受审,因为犯人最终会因审叛而死去,他不愿意送一个人去死。但又出于同情心他又一路护送。他们被反抗军俘获,当年在意大利并肩作战的战友对他说“你虽是我的兄弟,但只要逃跑,我便开枪”,战友告诉他,“这是战争,你必须选择你的立场”但达吕一如现实中的加缪一样,他没有立场,“我在这里出生,父母埋在这里,我一辈子也不离开。”在电影中,达吕说“对于法国人,我们是阿拉伯人,而对于阿拉伯人,我又是法国人”这是对现实中加缪的完美映射。
面对脚下的土地和荒谬的政治纷争,他们无从选择,唯有靠爱和同情来化解。达吕对政府军残杀俘虏深恶痛绝,对于反抗军的抵抗他也感到同情。在身份上,达吕和加缪一样是这个祖国的陌生人,而面对如此荒谬的世界,他们不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