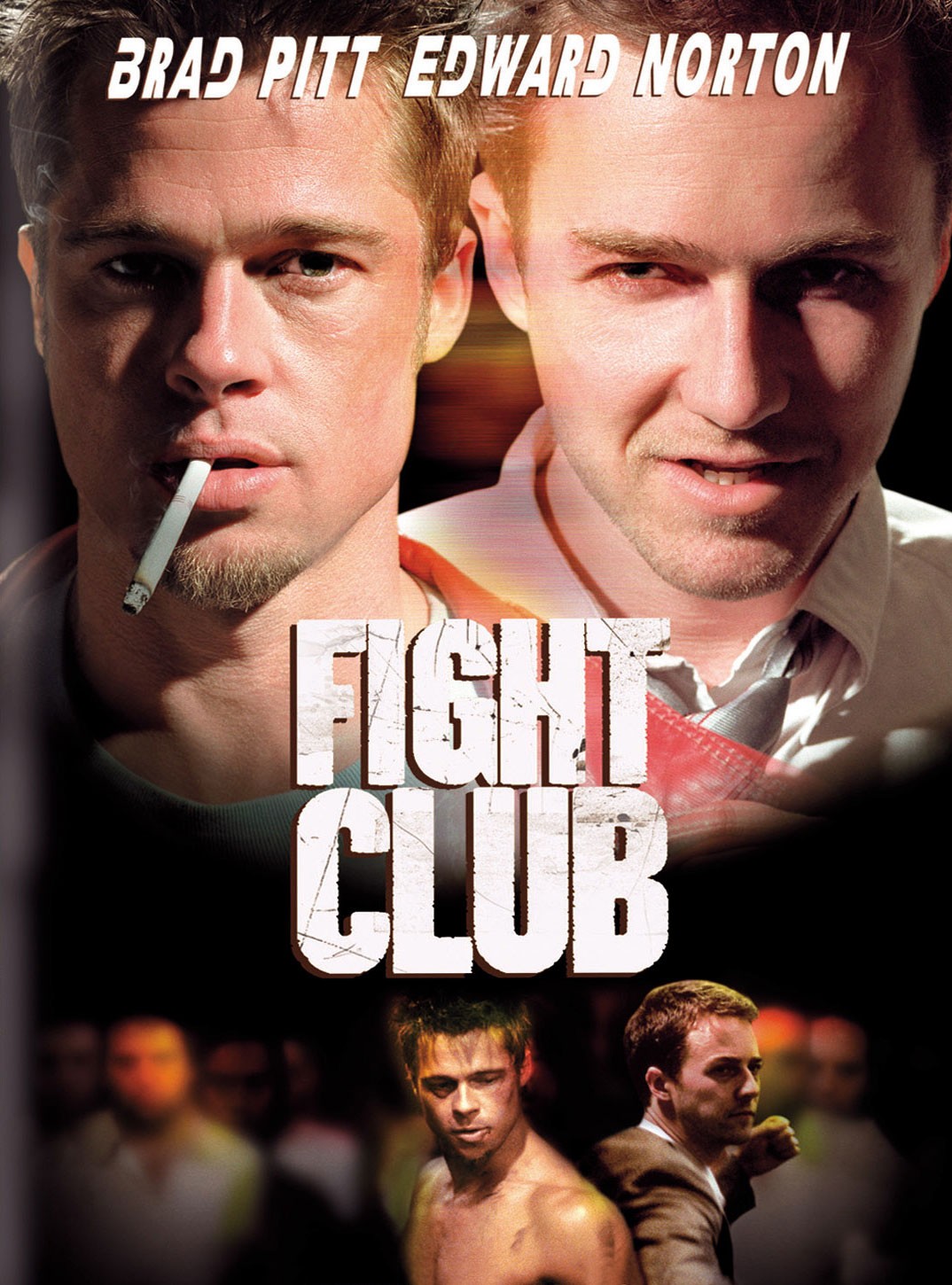
“广告诱惑我们买车子,衣服,于是拼命工作买不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代,没有目的,没有地位,没有世界大战,没有经济大恐慌,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从小看电视,相信有一天会成为富翁,明星或摇滚巨星,但是,我们不会。那是我们逐渐面对着的现实,所以我们非常愤怒。”电影中这样的台词比比皆是,分裂出的人格仿佛就是我们常态下人生的一个黑暗面,亦或者说是看待现实生活的另一个角度。
诺顿扮演的主人公杰克是被枯燥工作折磨、物质生活奴役的都市白领,失眠症带来的精神崩溃是都市生活压力的体现。工作环境的展示:硬朗粗糙的办公室灯光效果,整齐划一的工作服装,亮白色的单调办公环境,机械的镜头运动,以及一个个去行尸走肉般的人物走位。这种典型的现实环境把人变成了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彻底把人异化成现代工业的一环。人物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不断收集家具,空荡的房间里被摆上各种家具数码化的标签,崭新而百无一用的摆设是对于生活的一个巨大讽刺,反而把人限制在安逸的环境里,这种莫大的悲哀得不到主人公的认同。就如笼中之鸟,自由变成了一种束缚。
理想人格的出现是对于乏味枯燥生活的一剂烈性解药。音乐的变奏是最显性的直观体现,快速、暴躁、又极具诡异的混合型配乐,勾勒出人物内心的反抗情绪,对于这个毫无存在感的生活找到一丝自我价值的依傍。搏击——剧烈的宣泄,让人短暂的摆脱了现实的处境,找到了那种纯粹的、原始的力量与荣耀。组织——平等的群体让个人找到理性的皈依,圣徒般的虔诚更显迷幻色彩。犯罪——反抗权威、破坏秩序、挣脱桎梏,这种以自由为代价的行为充满自由的美感。电影中透露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犹如一剂迷幻药,将我们常态的认知彻底颠覆,犹如洪流一般冲刷着现代人脆弱的精神意志。成功洗脑之后就是一系列疯狂的破坏,试图摧毁禁锢人性自由的基础——物质,继而以一种“抛弃一切,拥有自由”的决心去开始全新的生活。
黑色主导了影片的走向。幽暗的街景,阴暗的人物,低调的灯光,肮脏、破败的屋景,哥特式的人物造型,对犬儒主义的崇高赞颂,对无尽绝望与幽暗意识的叙事主调把控,散发出黑色电影特有人性沉沦和无所适从的绝望气息。黑色电影的叙事模式带有很强的侵入性和腐蚀性,它就像一种高度传染的病毒,当它遭遇到其他的明亮、崇尚理性和温情的人道主义的类型,就会立刻将其占领,把这个类型改写成黑色电影门类中的一个下属类型。
大卫•芬奇的电影带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趣味性。本片的片头就极为风格化,构造了一个极富暗黑系的人体透视视点,移动幻影般的动态镜头随着神经网状的脉络肆意游走,加上暴躁急促的配乐处理,广告出身的大卫•芬奇用纯粹视听冲击就营造出了一个极富观赏性的前奏。对于悬念的设置导演使用了非线性叙事和独白补充叙事的技巧,一方面让观众摸不着头脑,另一方面又指引故事的走向,观众也许就成了他手中的玩具。影片中的人物独白有一种向观众强烈倾诉的欲望,导演将人物直接面对镜头与观众进行“交流”,试图打破隐形的“第四堵墙”,这种“间离效果”的使用直接作用在人物与观众的互动中,拉进了心理距离,在享受解密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至于被导演无脑的戏弄。导演自己也说过“我不认为电影就只扮演取悦观众,娱乐大众的角色,我的兴趣在于伤痕电影,有很多人认为我的电影是黑色的,是暗淡的,同时也有些扭曲,而我并非故弄玄虚,我只是想引发大家的思考。”
而我的思考是:纵你虐我千百遍,我待你依然如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