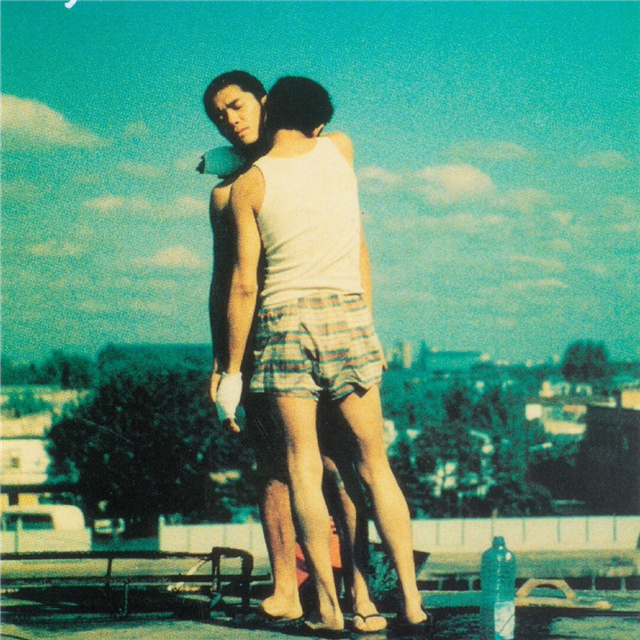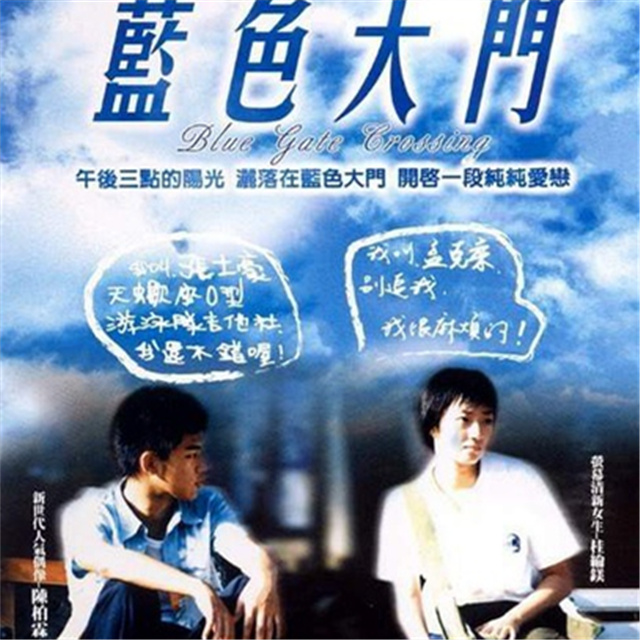近年来,“中国式西部片”的概念悄然兴起,从《西风烈》到《无人区》,在加上不甚成功的《决战刹马镇》和模糊各种类型的《让子弹飞》,虽然题材各异,但无论是黄沙滚滚、大漠孤烟的地理背景,还是恶人纵横、法制缺位的戏剧矛盾,打起“西部片”大旗的作品却又有着清晰的脉络。
我却以为,在这一类作品中最优秀的,却是从未给自己加上西部标签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是西部片吗?尽管很难下一个定义,但我们不难从这部影片里看出经典的西部元素来:渺无人烟的荒原、孤胆无援的英雄、猖獗无惮的恶棍和原始力量的对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可西里》对故事性的弱化处理,又令其具有了反类型的特征。
在《可可西里》中,陆川放弃了曲折刺激的好莱坞式叙事模式——从处女作《寻枪》来看,他分明具备这种讲故事的能力。更不用说,他本身便是出身著名编剧家庭。
对戏剧冲突的弱化处理和非职业演员的启用,让本片具有浓郁的新现实主义风格,在许多镜头的处理和叙事的安排上,甚至采用了纪录片通常的手法。但这种简单、直率的表达却不显乏味,反而在直白中迸发出击中人心的力量。
在寡淡如水的剧情中,我试图为其梳理出两条明暗相见又互为表里的主线,一条明线是巡山队与盗猎者的争斗,另一条暗线则是人与天地的对决。
在明线叙事里,导演刻意淡化以队长日泰为首的巡山队员们之所谓英雄形象。对盗渔者的随意处罚、对收缴羚羊皮的私下售卖,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行为,看似削弱了队员们的正面形象,但却正是同样游走在体制边缘的他们无可奈何之下的生存智慧。他们既是为了那片美丽荒原不计个人得失的理想主义者,又是懂得为生存而变通的现实主义者。
为了追踪盗猎者,他们走进可可西里的深处,时时惊心,步步为营,所有的这些都似乎在为着最终的对决而铺垫。真正等到双方见面,却被设计得轻描淡写。伴随着一声枪响,一切归于沉寂,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
而在暗线之中,所有人类都显得那么渺小而无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暴风雪和流沙不理会没顶者的秉性是良善或恶毒,只遵循着最简单的物理原则,吞噬所有敢于挑战自然权威的侵入者。死亡随时可能发生,而在这种环境之中,更显出生命的可贵。
从两条线的缠绕交叉中,我们得以窥视全篇的主题,那就是生命和死亡的力量。人的生与死,藏羚羊的生与死。在求生本能和肩负责任与这苍茫天地间的巨大力量斗争之中,戏剧的张力油然而生,让观者为之吸引、为之感动,
从一场天葬而始,以一场天葬而终,陆川为电影设计了一种带有轮回意味的环形结构,昭示了这是一部关注死亡和见证死亡的电影。但无论是纪实性的镜头语言,还是极为克制的背景音乐,导演都显示出冷静和隐忍的一面。太多可以煽情的地方,陆川选择了以旁观者的身份平静叙述,那些应该批判的、应该讽刺的和应该歌颂的,他全部刻意拉开距离,交给观者去自己判断。
正因如此,本片才有了让人心脏震动的力量。
“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印,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在藏语里,可可西里是“美丽少女”的意思。而恰如其名的,这里几乎是中国最后一片未被人类所污染的处女地。但正如一位柔弱的少女,可可西里也是任人蹂躏的。盗猎者的魔爪从未停止在这片土地上肆虐,苍茫天地间,熙来攘往的他们,留下血腥的罪恶。
无论是尸横遍野的藏羚羊,还是倒在枪口下的日泰、窒息于流沙中的刘栋,可可西里一视同仁的见证着这些生命的陨落,于它,千万年也不过一瞬,人间喧嚣,更如浮云流水,不值一哂。
而导演陆川,也似这亘古不变的可可西里,编织着镜头下的故事,吝啬于给予任何表情与态度。好人命丧黄泉,坏人全身而退?世界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两分法。更何况,这更接近于当年事实的真相。
在《可可西里》位数不多的出场人物中,有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便是刘栋和马占林。他们分属两边不同的阵营,但比起其他脸谱化的角色,却有了更多人性复杂的一面。
从巡山队员集结时,刘栋便是姗姗未至,弟兄们摩拳擦掌,准备物资,他却一个人沉溺在酒乡与温柔窟里。对可可西里那片让人发狂的地方,他分明是有抵触的,但这是自己选择的路,是无法卸下的责任和重担。所以他去了,而且,和所有同伴一样,不顾艰险、不惮辛劳。
战友重病,他千里驰骋送回集镇,又觍颜去见他的女人,既是贪恋那具肉体的温暖,也是为了讨要些钱财。女人要走,他无从得知,但即便知道,大概也不会阻拦吧。他不是浪子,却更不是一个可以为女人带来安定的男人。
他是队伍中唯一的汉人,天葬不是属于他的信仰,所以他拥有了一场更加原始、更加自然的活葬。突如其来的流沙,一点点吞噬着他的身体,从挣扎、恐惧,到释然,甚至微笑,刘栋求来了永恒的解脱。而他的身体,便如同亿万年来可可西里上所消逝的其他生命,渺然无踪。
而马占林则更像是对冷漠无知的民众的一种讽喻。他和他的儿子们不是大奸大恶之徒,不过是为了五元钱一张的剥皮费,跟着盗猎者们混口手艺饭。在巡山队的枪口下,他们瑟瑟发抖,为讨要一个冰冷的馒头而卑躬屈膝。被赶到大风大雪中自生自灭时,他们又用卑贱而顽强的生命力挺了下来。
为了区区蝇头小利滥杀生命固然可耻,但在巡山队员受伤时,他毫不犹豫的让儿子采取急救措施。而当日泰身死后,也只有他,久久矗立在尸身旁,眼神中说不出是同情、怜悯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们就像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既有善良、慈悲的一面,却也有着湮灭道德底线的人生哲学,既能顽强的战胜狂暴的自然,又会在强权和强盗面前毫无尊严的苟活。
而与之相对的,是真正有着清晰价值观,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巡山队员。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藏族同胞的淳朴,更重要的,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与早已将一切信仰当成牛鬼蛇神打入十八层地狱的汉族相比,藏人的信仰是坚定的。在世界屋脊的荒蛮之地,仍有着磕长头的善男信女,有着虔诚笃信的藏人。很多时候,信仰是一个人道德的支架,是对这个世界最后和最高的畏惧和敬服。所以说,失去了信仰,或者说信仰已经世俗化和政治化的民族是可悲而可怕的,不惧业报、不虑因果,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
藏民的天葬虽然看似残忍,却昭示着生命的真谛——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从“无”中诞生,也回归到“无”的状态。不用费心费力的预备墓碑、坟地,而是主动投身到大自然的代谢轮回之中。除开情人故友的回忆,再也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大象无形,无牵无挂。
作为第六代导演中的一员,陆川的风格偏向写实,但又极具浪漫与文艺情怀。这种风格上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可可西里》上,是叙事上的现实主义和表现手法和主题上的浪漫风格。他既用避免刻意拔高的平实手段,将自己和主旋律歌功颂德的传记电影区分开来,又赋予影片一种苍茫、野心的气质,使电影充满了浪漫化的视觉效果。
经历了巨大争议的《南京南京》和口碑平庸的《王的盛宴》之后,陆川似乎有些低调起来。明年,他所执导的第一部商业大片《吹灯传说》即将问世,在这部注定成为话题的电影里,不知一贯都很有自己想法的他,又能带给我们怎样的观影体验,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