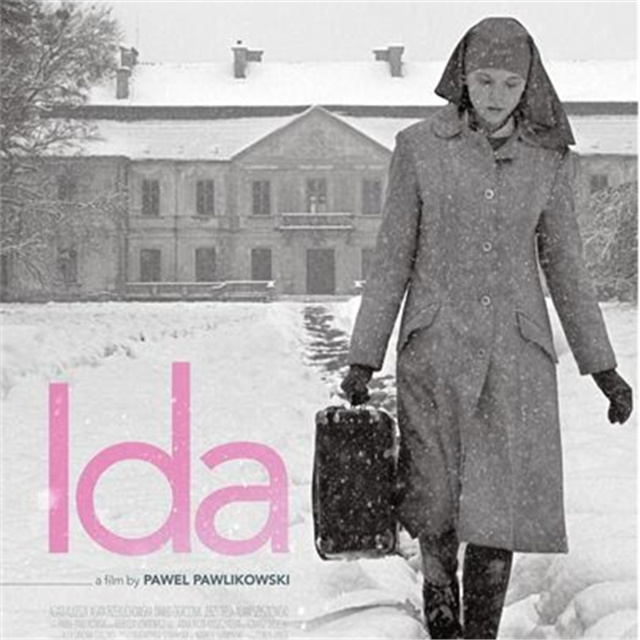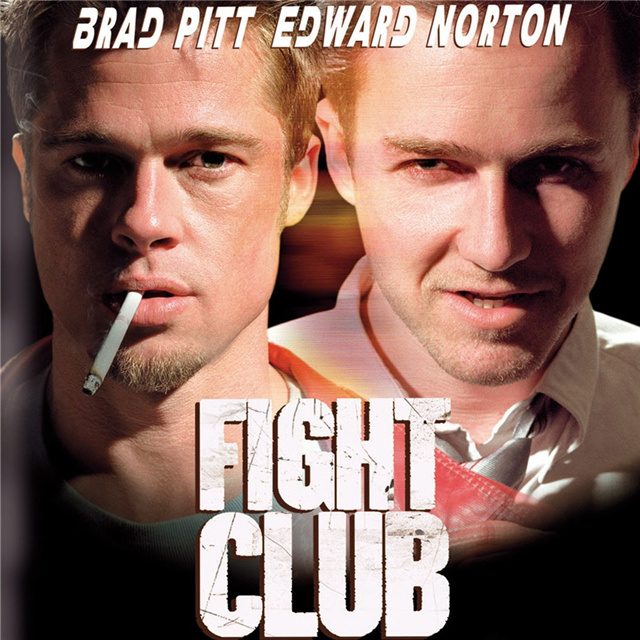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钢琴家》是根据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的回忆录改编的。
斯皮尔曼是20世纪30年代波兰广播和咖啡馆界的明星,也是华沙被纳粹占领和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中产阶级的一员。
斯皮尔曼在战后不久出版的回忆录,像其他类似的书一样,给人留下了一种关于大屠杀的深刻印象。
关于生存的叙述,即既有代表性又有历史性,他们立刻记录下了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历史灾难,并没有故意编造或歪曲事实。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
纳粹种族屠杀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没有活下来;20世纪40年代欧洲犹太人的典型经历是死亡。
一个主要的流派允许后人进入这个时代,因此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具代表性的画面。
我们自然会认同这些书中的主角,以及以他们为原型的电影和戏剧中的角色,所以想象自己会是幸运的那类人,即使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还用一种虚幻的信念安慰自己:如果我们当时在场,我们会勇敢地反抗纳粹,冒着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们的受害者。)如果没有奇迹出现时那种令人不安的多愁善感,人们就会用一种深刻而痛苦的荒谬感来看待生存——无论是靠的是愚蠢的运气、适应能力、陌生人的善意,还是这三者的某种结合。
1939年9月,德国人抵达克拉科夫时,波兰斯基还是个犹太孩子,他用阴郁、尖酸的幽默,用冷嘲热讽和同情兼而有之的无情客观性,讲述了斯皮尔曼的故事。
当死亡被如此系统地、如此任性地分配时,生存就成了一种笑话。
在影片结尾,由阿德里安布罗迪(Adrien Brody)精彩饰演的斯皮尔曼变得像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笔下的一个瘦骨嶙峋、存在主义的小丑,手里拿着一罐泡菜,步履蹒跚地走过一片荒芜、满目疮痍的土地。
他就像是一个关于深不可测的残酷的宇宙笑话的笑点。
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经历,波兰斯基先生以一种冷静、强烈的权威来处理这些材料。
这当然是最好的波兰斯基在多年来所做的工作(不幸的是,这并不是说很多),也是为数不多的nondocumentary关于生死犹太人在纳粹的电影,可以明确的(这是说很多)。
而且,自相矛盾的是,这是通过实现谦逊的,故意的意图来讲述一个人的故事,重建一个特定和有限的事件集来实现的。
(罗纳德·哈伍德(Ronald Harwood)的剧本确实对斯皮尔曼的描述做了一些必要的自由处理,但从电影叙事的要求来看,这些做法似乎是合理的。)他想要创造一个全面的视角——一个足以描述大屠杀的单一场景——的雄心最终击败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令人钦佩、严肃的《辛德勒的名单》。
波兰斯基通过展现历史的狭窄片段,制作了一部比斯皮尔伯格的影片更干巴巴、更有共鸣的影片。
波兰斯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可以被称为(悖论不断增多)人道的施虐狂。他一直着迷于发生了什么弱,普通人——米亚·法罗在《罗斯玛丽的婴儿》,“例如,或者杰克·尼科尔森在“唐人街”——当他们被邪恶势力侵入比他们更强大,他惩罚他的演员,剥去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展示人类在胁迫下的脸。
从10年前的《小山之王》,到最近的《山姆的夏天,餐厅》和《面包与玫瑰》,布罗迪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他机智、近乎自作聪明的自大。
在《钢琴家》的第一部分,他笔下的斯皮尔曼有一种得意洋洋的花花公子的步态,还有一种把魅力和好运视为与生俱来权利的男人自鸣得意的微笑。
当他在一个播音室里弹钢琴时,一场爆炸震动了整栋建筑。他蹲下,擦去袖子上的灰泥,继续演奏。后来,斯皮尔曼拒绝让德国入侵引起的广泛恐慌影响到更紧迫的事情,比如勾引迷恋明星的年轻女子多洛塔(艾米莉亚·福克斯饰)。
随着历史的发展,德国占领者和波兰斯基一起密谋抹去波兰斯基脸上的笑容。纳粹接管之后,斯皮尔曼一家被剥夺了财产、尊严(年迈的父亲,弗兰克·芬利饰演,因为敢走人行道而被一名德国士兵殴打)和他们的家,随之而来的是一段迅速、残酷的侵犯和羞辱史。
和其他华沙犹太人一样,他们被赶进犹太区,成为被囚禁的劳动力,遭受着疾病、饥饿和折磨他们的人随意的暴力的不断屠杀。
40年来,波兰斯基第一次在波兰工作(他也在布拉格工作),他以谨慎和清醒的态度重建了贫民窟的面貌和生活节奏。
你感受到了居民们的恐惧和困惑,你也观察到了他们直觉上徒劳的控制局势的尝试——发行地下报纸,通过墙壁走私违禁品,悄悄武装自己以抵抗。
生存本能表现为一种怪异的、麻木的、抗争与顺从并存的状态。而斯皮尔曼对死亡的逃避包含了勇气、被动和傲慢的奇妙组合。
他是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送往集中营的人,后来他成功逃离了贫民窟。1943年犹太人起义期间,他被锁在城市非犹太人区一间安全的公寓里,他从窗口无助地看着游击队员们开始了他们勇敢的、注定要失败的抵抗德国侵略者的战斗。
《钢琴家》在纽约和洛杉矶上映,成了幽闭恐惧症和超现实主义绝望的杰作,波兰斯基无情地把他的斯皮尔曼剥得只剩最赤裸的人性。
他既不是一个特别英勇的人,也不是一个完全有同情心的人,到最后,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动物的状态——病了,憔悴了,吓坏了。
然而,影片的高潮部分提供了最具戏剧性的悖论:让我们一瞥文明的冲动是如何在空前的野蛮中生存下来的。去年春天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在戛纳(,赢得金棕榈奖),我认为皮尔曼的遭遇,在战争的最后一天,与一个酷爱音乐的纳粹军官(托马斯·Kretschmann)追求情感通过将艺术的爱与道德尊严,一个方程纳粹自己,沉浸在贝多芬、瓦格纳、完全驳倒。
但再看一遍,就会发现,在肖邦令人陶醉、悲伤的音乐伴奏下,这一幕既痛苦又荒谬,证明了上世纪欧洲的灾难是多么的离奇。
斯皮尔曼可能是一个可怕的笑话的靶子,但最后笑的是他——恰如其分地面无表情。“这一切结束后你会做什么?”警官问道。“我会在波兰电台弹钢琴,”斯皮尔曼回答说。他就是这么做的直到两年前他去世
《钢琴家》为R级(17岁以下需要家长或成年监护人陪同)。
它有许多极端暴力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