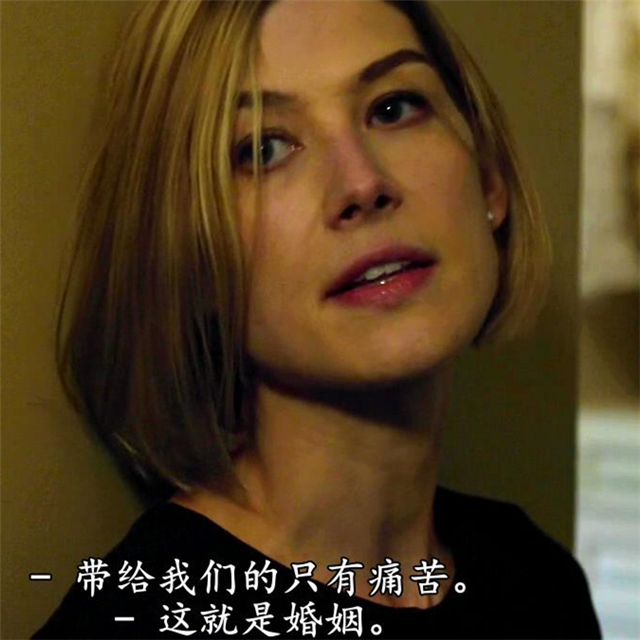近来披览晚唐诗,恰读到高骈的绝句,翻来翻去,还是“坐看青竹变琼枝”最合我心意,犹有皓雪扑面、澄目洗耳之感;虽不着一“雪”,却能在人心上造一个浩荡无边的洁白世界来。高氏之意显然在于以白雪寄喻这茫茫的人间世,而我却想,呆呆望着这青色的杆竹不自觉间便倏尔垒上了雪团,成了负累满满的“琼枝”,不免有些怅惘。这种隐隐的伤感竟莫名与去年看电影《落在香杉树上的雪花》的感受暗暗相合,好像它们隔着时间空间的河岸竟处在同一个冬天的同一场风雪之中。片中的伊斯梅尔也好、初枝也罢,都是那一杆杆青竹,在历史的风雪里变成了琼枝的模样。
《落在香杉树上的雪花》的叙事手法,似也是隔着一层雪雾。时空的交叉让回忆不断闪过,本来简单的故事到导演斯科特·希克斯的手下变得隐晦而复杂,现实和往昔的段落在电影中相互纠缠,有时竟至于难分彼此。美国男孩和日本女孩的两小无猜不啻是片中最柔软的部分,好像是追忆,是伊斯梅尔留恋着的过去的时光,是某种意义上对灵魂的放逐;而又仿佛就发生在当下,轮回式地让同样的雪花降落在同一棵香杉树上。或许伊斯梅尔在战场上丧失一只手臂的情节应当被大肆渲染,因为这是影片所需要的冲突点之一;然而这些却被描摹得很淡,甚至时而让人觉得,伊斯梅尔的左臂袖筒并非是空荡荡的,倒不如在表现年幼的二人在丛林山洞中竞相舔舐岩下滚落的露水时,对他们舌头的大特写更能印刻入人的内心;那柔软灵活的肉体上密布着的味蕾清晰可见,直白地暗示出少男少女性的萌动——灵与肉在此时合二为一,他们青春的滋味就如同舌尖上露水般甘冽,滋润着两个懵懂而饥渴的灵魂,也让他们的爱情在这个晦暗潮湿的角落生根发芽。
抽剥掉繁冗的政治背景和民族冲突,《落在香杉树上的雪花》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伦理的禁忌与世俗的偏见全都消弭在朦胧而富有诗意的影像之中。二人幼年时亲密无间的关系,在时过境迁之后却演化为一种微妙的隔阂感,而对美日关系的影射俨然成为了影片所不能承受的重量。我想《落在香杉树上的雪花》的野心并不在于反思战争抑或探讨人性;即便是导演有此意图,也被美轮美奂的摄影和对男主人公细致的精神刻画抢去了风头。伊桑·霍克的个人特色在片中几乎被削减去大半,却留下了一双深邃的浅蓝色瞳仁,在这善于捕捉世间大美的镜头下,与满目的皓雪相互映衬,在忧郁的气质上更增添了一份忧郁。伊斯梅尔跑过了幼年那个濡湿潮热的雨林,又跑进了如今这个皑皑茫茫的雪地,目睹着他的初枝从青梅竹马的恋人变为宫本的妻子;初枝的扮演者从铃木杏到工藤夕贵的转换,似乎也昭示着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当伊斯梅尔与初枝在法庭外的雪地相拥时,雪花落在他的礼帽上、肩上、空袖筒上,他才真正收回了自我,才让对迷梦似的逝去岁月的百般眷恋像雪花一般消融。尽管落满了雪花,但青竹仍然是青竹、香杉树仍然是香杉树——夏日疯狂生长的香杉就像浑身散发诱惑力的初枝,汗水和露珠混合着让她的碎发黏在雪白的膀子上;而冬季银装素裹的香杉是那个站在法庭门口的宫本之妻,此时雪花正悄然飘落在她的笑容之上。